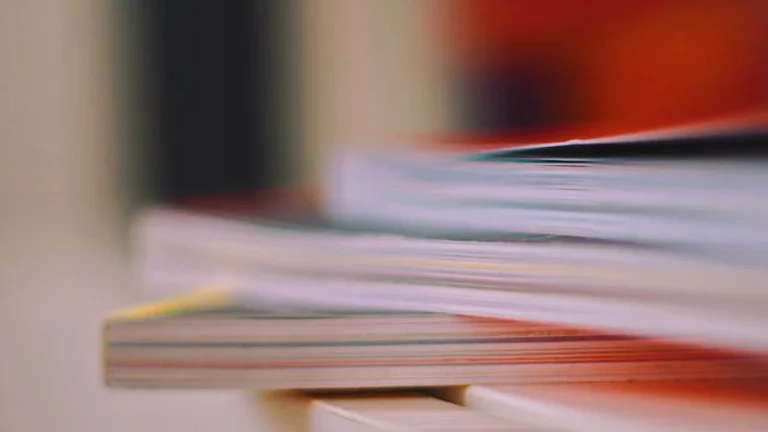直到1930年代,明恩溥的论述主导英语世界对中国人观感的情况才开始发生显著改变。1931年,曾为在华美国传教士的赛珍珠(Pearl Buck)出版了其成名作《大地》(The Good Earth)。该书以赛珍珠此前在安徽农村传教所接触的中国乡村生活为基础,描写了安徽贫苦农民夫妇王龙和阿蓝各种苦难的生活经历和通过勤俭努力而发家的故事。多年前我读完此书后大为震撼。书中两处冷静直白且详尽细腻的描写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至今难忘。一处是王龙所在的乡村世界因饥荒而出现的各种令人不忍卒读的惨剧。另一处是本为地主家奴才的女主角阿蓝在自己家里生孩子时的令人紧张得冒汗的险情。不管遇到什么天灾人祸或者困难挫折,王龙和阿蓝夫妇都靠着默默的坚持和不知疲倦的苦斗一一克服。这些朴实无华的话语与王龙和阿蓝所代表的朴实无华的乡土社会和大地田园相映成趣,真实活波、深刻感人地再现了中国农民的那种超乎寻常、几乎举世无匹的忍耐力、意志力和生命力。《大地》于1932年获得普利策小说奖,同年被改编成百老汇剧,1936年又被改编成电影,后来再于1938年帮助赛珍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美国人和英语世界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认知由此大幅改观。赛珍珠也就顺理成章地接替明恩溥的位置,成为英语世界有关中国人品格与特质的最重要的代言者。
在20世纪上半叶,除赛珍珠外,改变西方人对中国人品性看法以及中国人自我认知的还有辜鸿铭和林语堂。部分是为了回应明恩溥对中国人品格、个性与文化的评论,辜鸿铭于1914年在英文报纸《中国评论》发表系列论文,此年将这些论文汇编出版,英文书名是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文题名为《春秋大义》。辜氏在书中把中国人的性格特点总结为温良(gentle),大肆赞扬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和中国人的美德。林语堂的英文著作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中文翻译为《吾国吾民》)是应赛珍珠的建议写的,1935年在美国出版。林氏的作品对中国人的品格有褒有贬,强调中国人的温顺、忍耐、冷漠、老于世故、和为贵、知足和保守等特征,不过, 林氏著作的总基调还是认为中国文化是独特且伟大的,体现出爱之深、责之切的关怀意识。在赛珍珠的大力推荐之下,林氏的这本书成为美国的畅销书,进一步深化了英语世界对中国人品性的全面了解。辜氏和林氏的这两本书后来又分别都翻译为中文出版,当然也随之掀起一股中国人认识或反省自己的热潮。
这些有关中国人品性的深具影响力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立足于对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观察之上。明恩溥和赛珍珠以不同的文体和风格直接刻画了中国普通农民的特质与个性。而辜鸿铭和林语堂的作品虽然更像是一般的文化评论,其解说和谈论的对象却也都是中国乡土社会上至官僚士绅下至一般农夫的各色人物。在笔者看来,在这四位的作品中,赛珍珠的小说最富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深沉的感召力,能够直击读者的灵魂。赛珍珠对阿蓝的描写尤其精彩,时常让我想起小时候同村的那些最不起眼或者最不幸的农村妇女。她们在极端困苦的处境中,依然不屈不挠地担负起妻子、母亲和女儿的神圣职责,在忍辱负重中拼尽全力为家庭争取哪怕一丝一毫的希望和转机。正如我在“做一个有教养的现代中国人”一文中谈论中国农民时所说,他/她们“每一代人的经历都可能是平淡无奇甚至窝囊委屈的。可是,我们如果把之前所有世代的先辈们加在一起,就会感到相当震惊并肃然起敬:连续几千年的生命链条是如此地坚韧有力,其中凝结着怎样的艰苦卓绝又波澜壮阔的生命史?!又成全了何等不绝如缕、永不言败的盼望?!他/她们作为个体是卑微柔弱的,群体的他/她们则配得最高的赞誉和讴歌。”
很多中国人认为西方人不了解中国人。就凭赛珍珠对中国农民的描写,我认为这一评价至少是不全面的,因此也是不公正的。就揭示中国人内在的品性而言,至少在自己有限的视野里,我还没有看到近现代哪个中国作家或文化评论家能够写出达到《大地》水准的作品。赛珍珠以及明恩溥的眼光是非常锐利且深邃的,他/她们都抓住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特点。西方文明最为推崇的人物是荷马史诗所描绘和颂扬的战争英雄,这些贵族英雄们以其勇敢无畏的开拓性、冒险性举动成为后世西方人模仿的楷模。这些英雄情结一直弥漫于古罗马的征服行动和后来的西欧封建贵族体制,深刻地影响和塑造了西方人的品格与个性。中国自宋代以来便进入平民社会,自耕农社会事实上构成了中国文明的主干。自耕农的品格与个性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中国文明的品格与个性。赛珍珠和明恩溥作为美国人之所以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抓住中国人品格与个性的若干重要侧面,也许与美国本身没有贵族传统以及美国深厚的大陆农耕文化背景有关。美国1900年的城市化率只有40%, 到了1940年才达到56%。无论是家庭传承还是社会环境,1930年前后的美国人对乡土社会和人情并不非常陌生。2020年,美国和中国的城市化率分别达到80%和64%。现在的美国人可能非但写不出赛珍珠那样的作品,而且可能也无法理解《大地》里的中国人了。
明恩溥和赛珍珠将观察目光定睛在中国普通农民身上,还具有另一个极其重要的意义。他/她们开启了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新方式和新视角。他/她们的目光远离皇帝大臣或者官僚士绅,他/她们不依赖于经典文献或书本知识,反而却专注于观察普通人的现实生命状态和生活状况。这一点可能与美国的共和传统有关。美国的开国元勋托马斯 杰斐逊便认为,独立自足的自耕农才是共和国最好的公民。笔者认为,中国漫长的历史也已经证明,独立自足的自耕农是中国文明最好的载体和传承者。在与天地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中国的农民模仿追随天地自然之道而形成了独特的品格与个性。他/她们在顺从中隐藏着力量,在忍耐中培育着勇气、在坚韧中履行着使命。他/她们滴水穿石般的努力最终成就了中国文明的博大、持久和辉煌。尽管明恩溥对中国人的“国民性”履有批评,在后来出版于1907年的《中国的兴起》(The Uplift of China)一书中,他反倒认为,中国人的品格与特性使他确信中国文明会有光辉的前景。不知道这是不是第一部讨论中国崛起的著作。不管怎样,这些作家和评论者所观察和刻画的中国农民的品格特征构成了中国人品性的基础,也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人和当下中国社会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角度和洞见。
相关阅读: